老家方言,把父亲称做大,一声。芬她大,就是芬的父亲。芬她大是我姥爷的二哥的大儿子,也就是我母亲的堂哥,我叫他大舅。芬还有个弟弟,叫钢蛋,所以芬她大也是钢蛋他大,但印象中很少人叫钢蛋他大的,自然这是因为芬是老大,芬她大已经叫顺口了。
芬她大很能干,会好多手艺。我记忆里有他在村东的岭上起石头的画面,一个人坐在采石坑里手拿锤头和钎,叮叮当当地打,打得石头上冒火星子,把石块打成长方体,拉回村给人垒墙盖屋用。是的,芬她大会盖屋,我们家盖新房子时他就来搭过手,和泥砌墙,安门上梁扇屋顶,样样都行。村里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办酒席时,厨房里也少不了芬她大的身影,他多少算是个厨师吧。不过,回忆起这位大舅来,让我最难忘的,还是他在村东的田里赶牛耙地的画面。
耙是旧时农村里常见的农具,样子就像一张去掉床腿的木床架,但框架中间只有两根横梁,立起来看是个目字。耙的底面钉有巴掌长的铁齿,一根一根地立着,叫耙齿。我小的时候牙长得不好,我妈就取笑我豁牙耙齿,用的正是这个耙字,十分形象,也由此可以想象耙齿的样子。
秋天庄稼收割之后,田需要耕。耕地先用犁,将块结的地翻起来。犁过之后,再用一种铁盘犁滚一遍,把土块切碎,这时的田就平整多了,但还不够细,不能播种,此时就要请耙出场了。耙的作用就是把地再松一松,把土块进一步粉碎,把碎石给梳出来。耙用牛拉,两三头牛一组,牛在前,耙在后,驾耙的人站在耙上,一手牵缰绳,一手握皮鞭,驱赶着牛缓缓地向前行,就像行船,在水面上迎风前进,很威风的样子。这个威风驾驶员就是俺大舅芬她大。大舅在生产队里管喂牛,赶牛耕地也得他来干。他在村东的田里耙地的时候,我和表弟表妹们喜欢跟在后面追着玩,瞅他不注意就跳到耙上去,被他斥下来再伺机上去,乐此不疲,那行驶的耙实在令人着迷。有时也在远处看,听他唱赶牛的小调。那小调有点像蒙古的长调,在安静的田野中能传出很远,非常好听,如今我稍加回忆,那调子便远远地在脑中浮现,同时伴着故乡田野的气息。曾经尝试把调子记下来,看看能否弄出个谱子,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发现根本做不到,因为一旦想回忆清楚那调子,调子立即就变了形,无法捕捉,记忆真是很奇怪,这令我想起袁枚《祭妹文》里的一句: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这个“逼取便逝”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吧。
说起这段小调,又想起许多年前我给两地分居的老婆鸿雁传书时,有一封信中就提起过芬她大的赶牛小调。那时的我张口就是文艺腔,记得说那曲调中有一丝哀怨,像一条金色的小蛇飘荡在北方寂静的田野云云,描述得颇为生动,但有一股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劲儿。要说俺这大舅其实一点浪漫气质也没有,十足的村夫庄稼汉,他就是唱给牛儿听的,牛儿听了能安静地劳动不耍脾气,赶牛耙地都得这么唱,是个传统,也算个技艺。但那曲调能如此长久地驻留在一个孩子的心里,让几十年后的我仍然会时不时地穿越时光隧道去回望当年的情形,可见大舅的演唱中必有一种魔力,而这种魔力,我多年以后又不断地遇到,有时是一支曲子,是一首歌,有时是一幅画,就在你听过一次或看过一眼之后,那魔力即悄然附体,永生不去,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前几年回老家,到我舅舅家吃饭,舅舅说芬她大已经去世了,得癌症死的。到医院查出来已是晚期,住了一阵子院,经历各种化疗放疗,毫无效果,病情继续恶化,最后芬她大说回家算了,不要死在医院里。钢蛋就把他大拉回了家。回去当夜就不行了,舅舅说,那天晚上下大暴雨,一夜霹雷合闪,天亮时接到钢蛋的消息,说他大死了。我听完之后心里一阵感慨,又想了他的赶牛小调,不知如今还有谁会唱,会不会就此失传了。
大前年我父亲去世,钢蛋来送殡,我们见过一面。钢蛋说他在贩藕,到江苏和安徽收,拉回来在市场批发,也给饭店送货。藕在老家是酒席上必不可缺的凉菜,这些年吃喝风甚盛,对藕的需求增长很快,钢蛋说生意不错。而今,据说自从习大大上台后官场不兴吃喝了,不知钢蛋的生意还好不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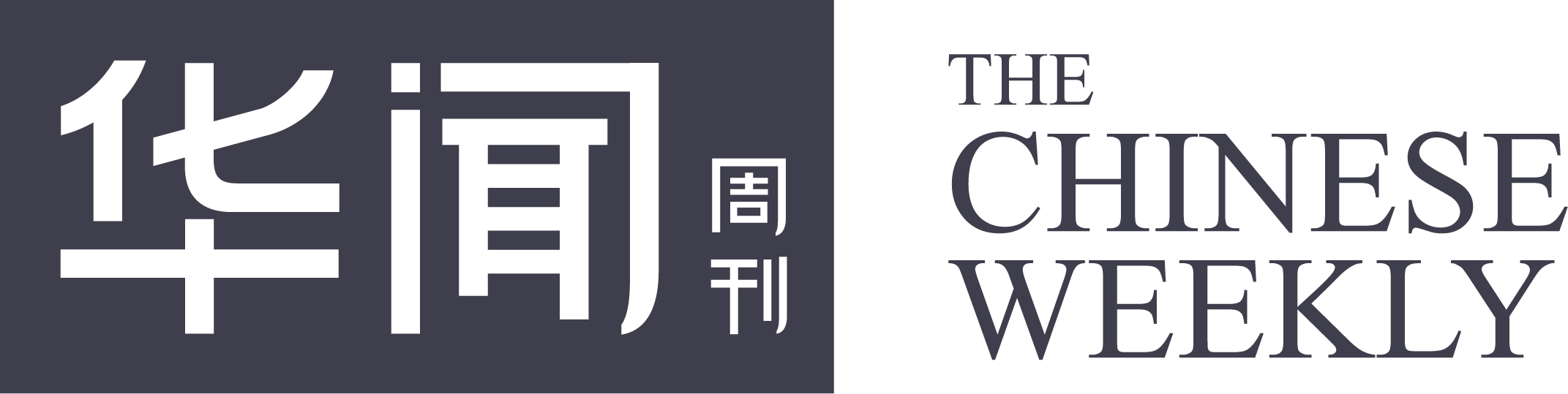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