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很好,要是再多点阳光就更好了!”望着窗外绵绵细雨,陈思诚和佟丽娅这对银幕金童玉女异口同声这么说。应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的邀请,陈思诚和佟丽娅来到伦敦,除了参加电影节颁奖典礼外,也趁机好好放个假。刚从澳洲飞到英国,经过二十小时的飞行时间,尽管两人仍为时差所苦,但脸上依旧透露出兴奋神色。
才踏上伦敦,小俩口抓紧时间观光,“英国跟想像中差不多,博物馆多,很有文化气息。虽然我们很累,但一下飞机就开始逛街,出门总是特别好,我们一直很high,到处都觉得新奇,而且一直拍照,因为这里拍照很美!”佟丽娅说得眉飞色舞,好似心还在外头。他们带着《北京爱情故事》走过许多国家,但英国是第一次来,所以还特别空出两天行程当个真正的“观光客”。在接受专访前,他们已经走过不少伦敦景点。

电视像小说电影像诗歌
聊起工作,两人收敛起笑容认真起来。不同于银幕上携手晒恩爱,陈思诚和佟丽娅分别接受访问,“我不愿意跟他一起拍照访谈,我们平时工作也是分开的。”佟丽娅打趣地说。她提到婚后这段日子,两人相处的时间其实不多,各自在剧组拍戏,“平时打电话联系,偶尔互相探探班,很少两个人一起在家闲着没事干。”佟丽娅表示,即使婚后全身心投入工作,两人仍是支持彼此的力量,“这种状态最好!有共同的爱好和事业,但也有各自独立的工作,有个人、有爱在那里,能互相理解很有安全感,做事也比较踏实。”言谈之中藏不住幸福感受。时至年底,佟丽娅工作行程已经满档,同时投入电视剧和电影的拍摄,“一回国马上有新戏拍摄,也要配合电影宣传,休息这么久,总不能一直玩,该工作了!”佟丽娅笑着说。
“回北京马上有电影的事要处理,明年‘应该’会有新的电影。”陈思诚也透露了自己的新动态,他将会带来一部全然不同于《北京爱情故事》的新作品,“我不愿意重复自己,下一部电影一定会做得不一样,我会不断尝试新东西,这对创作很重要。”陈思诚在访谈中透露,现在正进行悬疑类型的电影拍摄,他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我不安于只做一个普通的演员,也不安于预想得到的生活。正因为希望未知、希望挑战、希望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才去做这样的尝试,这是我自己要过的生活。”陈思诚眼神无比坚定,对电影的热情展露无遗。
从拍电视剧转换到拍电影,他有很独特的诠释,“电视像小说,电影像诗歌,其实两种我都挺喜欢的。但是若未来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我会更专注于做电影。”陈思诚解释电影数量比较少,用很小的篇幅描述很庞大的东西,虽然电视载体大,但电影涵盖的信息量比电视更大。听他这么说,在编剧、导演和演员三个身份,或许导演这个角色更吸引陈思诚?他回答编剧像是上帝的角色,一个人闷头写东西的时候,可以随意决定人的生死,“可以让人瞬间变成百万富翁或让人飞起来,可以任意编造故事,那种快感挺有意思的!”
导演的身份则十分不同,脑子里的东西如果变成真正肢体语言呈现出来,甚至比想像中效果还好,就能得到成就感,“尤其剪辑的时候,将声音特效所有元素加进来,像盖房子一样越来越丰满漂亮,那种满足感更强烈。至于演员,最过瘾的则是在片场演戏的时候。”陈思诚畅谈工作满溢兴奋之情,他总结:“不同的事情会带来不同的快感,当然每个角色乘载的压力困难也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去想哪一个最喜欢。” 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每一种工作挑战都充满热情与干劲!
同为演员的佟丽娅一样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她演过多部电视剧,诠释过不同角色,每一个都有着全然不同的性格,佟丽娅说:“每个角色我都非常喜欢,她们都拥有自己的闪光点,这些角色多少都有我自己的影子。”她接着解释自己接戏前会先一一筛选每个角色,因为自己想演,所以每当离角色越来越近时,会特别开心,她同时能从这些角色中学习和成长。她说自己在拍摄过程中很容易入戏,但她不会把戏里的角色带到现实生活,“我算是一个理智的人,而且性格爽朗,容易跳进跳出分得清楚,不会沉浸在戏里难以自拔。”对于婚后选择工作角色,佟丽娅认为,两人都是专业演员,婚后依旧支持对方的工作,不会受影响,陈思诚也表示两人平常工作上较少进行讨论,“彼此出出主意,看她后面接什么戏,我帮她参谋参谋。”然而,问及未来是否有规划像《北京爱情故事》一起合作演出,他们不约而同表示没有再次合作的计划,“我们喜欢的题材类型不同,很难碰在一起。先做好自己的事吧!我也很愿意跟更多不同的导演合作。”佟丽娅这么回应。虽然短期内看不到两人同台演出,但对彼此的工作建议却格外重视,陈思诚不假思索地说:“她肯定是我剧本的第一个观众,让她用女性的普通观众的角度看一看有什么样的感觉。”
做一个游戏心态的电影玩家
《北京爱情故事》是陈思诚首次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剧本编写过程完全没有经过与他人讨论,他分享了一开始想做电影的想法,“这部电影是个特别个人的东西”,他在泰国拍戏时用三个月时间完成编剧,“那时候一直纠结于多线叙事还是单线叙事,我一直很喜欢导演诺兰(Christophe Nolan)的电影叙事结构,想有一些尝试和突破。所以我选择用‘在一个空间里讲时间的故事’这个方法。空间的方法是指大家在一个空间各自生活,虽然是同一个空间,但是大家看完后能有关于时间的感受。这是我一开始创作的初衷,但我不知道它让多少人感悟到了。”
对于电影里五个年龄阶段的爱情故事,陈思诚认为那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故事,“就像我们喜欢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自己,没有办法只喜欢哪一个,因为都是你自己,你不愿意面对的不美好或你想面对的美好,都是你自己的客观存在。”他顿了顿,眼神专注地解释着,“青年那一段是最难的,因为它涵盖的信息量最大,包含青年一见钟情的激情,但又要承载激情后面对现实考量的问题,所以承担的任务会复杂一些,不像青少年那么简单、也不像老夫妻那么纯粹。”然而,佟丽娅则说自己特别喜欢孩子那段故事,她说“我是思诚写完第一个读剧本的人,一看完我立刻发信息告诉他‘小孩能看到别人背后的光这个点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佟丽娅用了三个“最”强调她对这个桥段的肯定,她说有时候看到幸福的人或是善良的人,会感觉他在人群里真的能散发光芒。“我们经常会这么做比喻,但陈思诚把它形象化展现出来,传递了一些真善美的东西,为文艺作品带来正面能量。”
陈思诚的电影导演路刚起步,对于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电影,他也曾纠结困扰。在市场、奖项或者自我表达等前提下,许多导演前辈已经做出选择,那陈思诚呢?他思考一会儿后这么说:“我也曾受困于我该怎么做?但后来我觉得人生挺短暂,我不用受困于任何类型或结果,要回到想拍电影的初衷,不外乎是你有想表达、想说故事的欲望,而且你爱电影行业,爱这个跟梦想最接近的东西。”他认为只要在不赔钱的前提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现实考量都是退而求其次的,“未来我更愿意做一个带有游戏心态的电影玩家或电影‘极客’(geek的音译),不会刻意地去迎合某一个方向,最重要的是我想做什么。”
他说以前会拿成功导演当做自己的目标,结果发现每个人的成功都有其个别独特的东西,是别人无法取代和效彷的,所以他现在没有特定目标,“我怀着像吕克·贝松(Luc Besson)初期的游戏心态,拍摄各种类型电影,像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卡梅隆(James Cameron)一样探索电影、热爱电影。我觉得做导演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可以对一个领域发生兴趣,并借助影片去研究他,拓宽自己的领域跟视野,这件事是有意思的。拍摄是一种输出,但人像硬盘,如果只有输出没有输入,一定会透支,人生一定要多看、多听、多感受,我认为人离开这个世界什么都带不走,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经历感受。”漫漫电影路,陈思诚走得心里踏实。
访谈结束之前,陈思诚和佟丽娅十分有默契地对这趟英国旅程下了注解:“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华语电影,同时也希望中国电影走出去。” 他们坚定地道出对华语电影的深切期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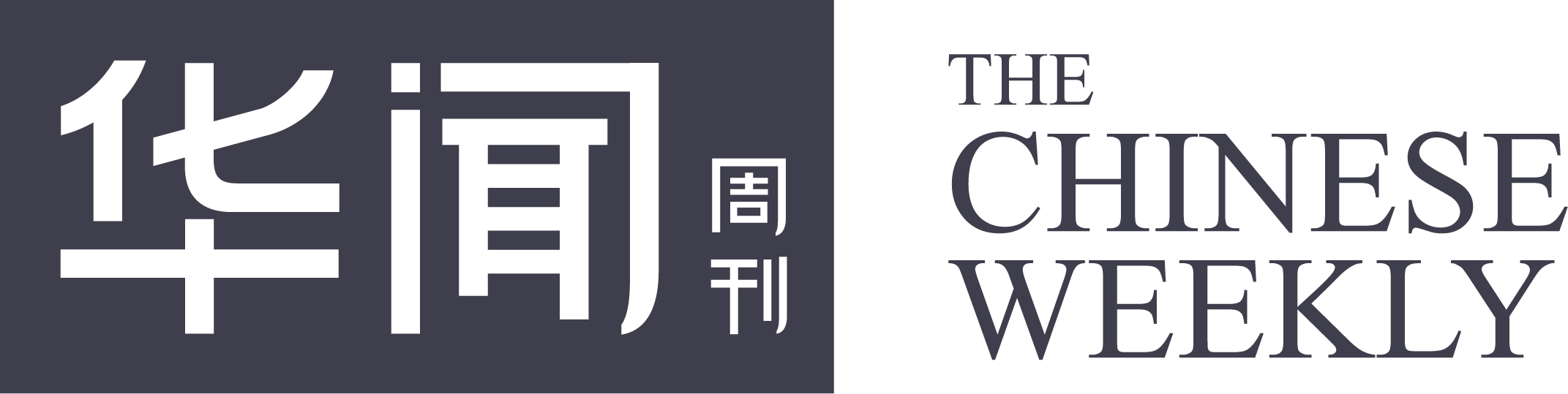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