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犇在昆明滇池喂海鸥)
小眼睛、双眼皮、大酒窝,牛犇给人的印象总是个快乐的小老头。从影70年,他从银幕走向电视,也未能免俗地参加了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年过80的牛犇,对演艺事业始终如初。“我还有很多角色想要出演。”他说。
在2014年年底,牛犇在伦敦的一家酒店接受了《华闻周刊》的专访。见面时,他西装革履搭配颇有时代感的贝雷帽,热情地站在门口。虽然此时的伦敦已寒风袭人,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牛犇的情绪显然并没受影响,只是在回忆前辈和恩师时,牛犇流下了眼泪。
1935年,牛犇出生于天津。那时他的名字还是张学景,现在已很少被人提起。6岁时,父母因贫病交加在同一天离世,可怜的牛犇连自己的生日都不曾记得。牛犇说他现在的履历表上填写的日期7月9日是他入团的日子,而生肖也是后来推测出来的。“他们因为死得早,也没跟我说,就把我的生日刻在床板上头,后来家里条件不好,把铺板给卖了,所以把我的生日也给‘卖’了。大家都不记得了。”
无奈之下,牛犇跟随大哥和嫂子赴北平 (现北京)投奔亲戚,可到了北京才知道,亲戚早已被日本人赶出了工厂。走投无路之时,哥哥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工作,还学会了开车。后来,哥哥被中电三厂(电影制片厂)录用为司机,一家人住进了厂区宿舍。从那时,牛犇便与电影结缘。
没多久,牛犇发现他们的后院住着许多有名的电影演员。他与谢添、韩涛、齐衡等著名演员每日朝夕相见,慢慢地都成了朋友。由于牛犇自幼机灵、活泼,手脚又勤快,乐于助人,这些演员都爱请他帮忙。也许命运注定牛犇要吃“电影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1946年,沈浮导演的抗日影片《圣城记》,需要一位饰演村童的小演员,在片中出演的谢添特地向沈浮推荐了牛犇。
10岁的牛犇开始涉足银幕,从此步入影坛。他饰演的“小牛子”一角受到众多著名演员的喜爱,大家也更爱用角色名称呼他。谢添就势替当时还叫张学景的10岁少年取艺名“牛犇”。犇者,跑也,取其奋发不停之意。

(《圣城记》剧组成员合影,牛犇当时只有10岁。)
恩师教诲永不忘
在70年的银幕生涯中,牛犇并未辜负众望,塑造了无数令人过目难忘的小角色,一生没有摆脱这个“小”字。“过去镜头里的主角都是高大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长得越来越不够标准。小时候,我演小艺人、小学徒、小丈夫;青年时期演小战士、小工人;到了现在,我演小老头。”
1981年,46岁的牛犇喜获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之后连续三届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殊荣,但他仍不满意。 “如果我知道大家那么喜欢,可能还会更努力些。”到目前,哪个角色是你最满意的?“到现在,我都在尝试不同的角色,也常常会想自己如果饰演某个角色应该如何演。人类是在不断进步和变化的,所以演员在饰演角色的时候也应该与时俱进。”
牛犇至今感恩于老艺术家们对他的栽培,“我现在不愿意去看旧的相册,因为过去很多老朋友已经仙逝了。可能昨天还可以跟他们谈天,今天却已无法再见面。最让我难过的是,我现在获得了一些奖项,我在大家的鼓励下还在努力追求着。虽然那些朋友他们现在也得了一些奖项,但他们自己已经看不到了。每次谈到这里,我就很难过”。说到这里,牛犇哽咽了。
据牛犇回忆,早年在拍《海魂》时正好遇到评级定薪,单位给他定级太低,牛犇当时的情绪自然受到影响。“赵丹对我说,演好戏是主要的,不会因为你的级别高低而定你的戏好戏坏。观众喜欢一个演员不是因为你的级别,而是你的戏演得好不好。别闹情绪了,好好演戏才是最主要的,有些事一定要看得淡一些。”这席话令牛犇终生难忘。

卖命牛犇
牛犇演戏认真是出了名的,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角色,不管戏多戏少总要人物出彩。他在自己的黑色硬皮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最近十几年他扮演过的所有角色档案。研读剧本时,牛犇首先要让角色的台词说人话。在征得导演的同意后不断修改自己和对手的对白,做到既符合生活又符合人物性格。
在拍电影《飞越老人院》时,由于档期的原因,牛犇最后饰演的是一个无台词、瘫痪在床的中风老人。导演张扬给他安排的角色是躺在病床上不用动的,牛犇认真读过剧本之后觉得这样的设置不妥。“我给导演提了个意见,我不能躺在那儿,我要坐着演。我看到过这样的病人,躺时间长了容易得褥疮,用绳子吊起来,绳子用力,而不是腰使力。”后来导演又根据这个设置增加了一些寓意的东西。“虽然不能说话,但可以发出一些喉音。演完这个,我的嗓子哑了一个礼拜。”在有限的镜头下,牛犇所饰演的这个不起眼的群众角色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巧手牛犇
牛犇对角色的较真没有让他对人生纠结。“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遭受牵连被发配前往上海市郊的化工厂劳动。他采取了柔性而不失智慧的生存艺术,在长达十年的下放劳动中,人尽皆知的电影明星转为普通的工人。牛犇当时愉快地接受了厂里派发的看管高危车间的任务,几年间未出任何纰漏。
“我有兴趣的事情很多,我都很乐意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比如打铁、木工、钳工、雕像……,我自己都可以完成。当时我们在南京拍一部戏《湖上人家》,剧组临时缺少一条船,剧情是男主角在回忆他在海里的情景。画面里要展现一个风帆,就需要一艘帆船的模型,结果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弄不到,结果道具说必须要往返一次城市,找专业人做,往返一次三天路程不说,花费也大。我自告奋勇,在两天内和一个木工把这个道具完成了。废弃的木墩子七砍八砍,砍成一个船型,再用刨子刨光。一次性筷子是风帆的骨头,这个船做好后他们立马拿去当道具了。”
在上影厂排话剧时,牛犇曾用收集来的几千个空火柴盒,把空火柴盒一个个串起来最后拼成一个圆台面,用牛皮纸贴起来上了清漆,既轻便又便宜。想不到的是,牛犇两个儿子幼年时的衣服也都是他亲手制作出来的。“我手很快,上午开始做鞋,晚上就能穿上了。里子、面子都会做。”

(牛犇赴香港拍摄《海誓》)
“傲气”牛犇
和牛犇塑造的那许多草根角色一样,牛犇隐匿在芸芸众生中,安然度过了最难熬的岁月。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他重回电影厂后,被聘用为上影厂电视部的创始人之一。
最让牛犇高兴的是他拍出了当时最长的电视剧——14集的《蛙女》。这是曾写过电影剧本《钢铁世家》、《家庭问题》的著名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又一个作品。他的《蛙女》在上海《解放日报》连载后,反响强烈。所以牛犇要把它搬上荧屏,并亲任导演。
从改变剧本、选择演员到具体拍摄,牛犇是全身心地投入。牛犇回忆说,此剧从今天看来可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在当时,确实红火过一阵。“公安局说,连当年的刑事犯罪案件都减少了。因为呼声太高了,电视台就把播出频率从一天一集改为一天两集。”
但令牛犇遗憾的是,在电视剧掀起了翻拍风潮时,《蛙女》却至今从未被提及。“在我的电视剧里,排位在前的有编剧和导演,没有顾问、监制什么的。我更是将道具排在职员表较前的位置。我觉得在制作电视剧时,道具组的工作很重要。电视是拍实景,实景就靠陈设。道具可以体现这家的文化、性格、经济基础和生活习惯。我根据职务在剧中的贡献排名。只要那些领导给我的电视剧提一个意见,我都会把他们的名字放进去。”
当牛犇正准备进一步大干时,“单位因为我在外拍戏太多,在我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提前撤掉了我的职务。”慢慢地,电视剧部也因为牛犇的离开关闭了。

(牛犇拍摄电视剧《我和丈母娘的十年“战争”》)
率性牛犇
牛犇的情绪并未受此影响,仍继续创作越来越多的经典“小人物”。除此,牛犇在2014年参与了电视真人秀节目《花样爷爷》录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口气能吃11片面包,爱吃冰淇淋,总与曾江“顶撞”的老顽童。
在采访中,牛犇也不避讳他和“老大”曾江的矛盾:“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性格是顽固的,不必强求,有矛盾也没关系。在巴黎的丽都秀上,曾江指导大家吃西餐的礼仪,我就不高兴了。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你凭什么来要管。还有一次,曾江主动给大家做鱼宴,我发现他竟然用洗手的水洗鱼,太不讲究了。”牛犇几次将“自以为是”的标签贴在这位好为人师的曾江身上。
两个半小时的访谈结束,牛犇率真的性格袒露无疑。他对表演和人生如“牛”一样的 “倔性”和执着使他受用终身。

(牛犇与张艺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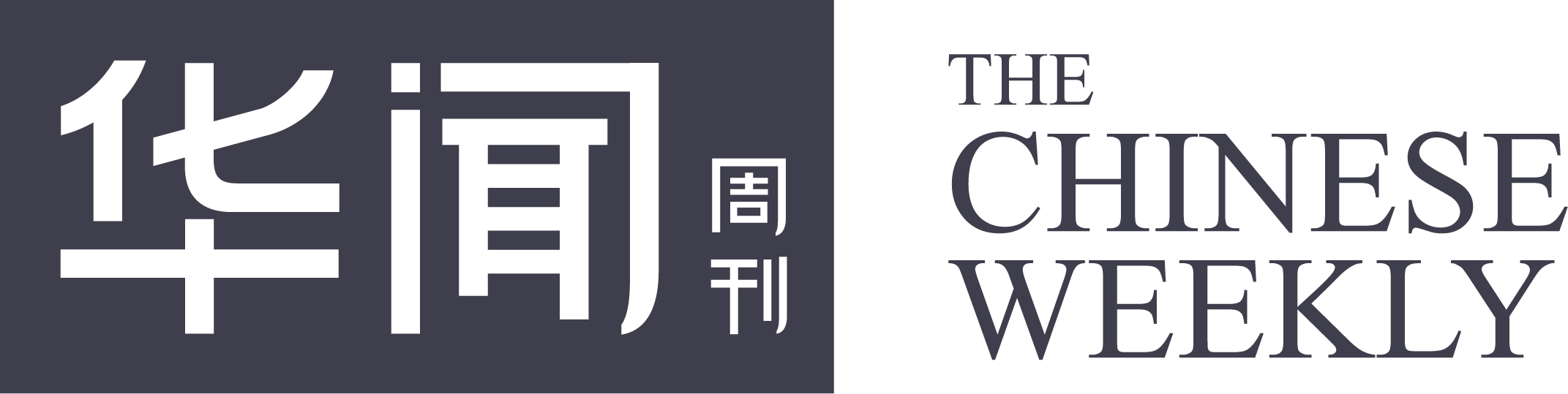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