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小萌拍摄的老北京自行车是一系列平实、耐心的照片。他的摄影项目并不炫技,也没有刻意往当下流行的某个概念里套。这种“不刻意、不炫技”可以理解为摄影师的一种自信。

这一摄影项目的起点,赵小萌告诉我,是发觉老北京自行车在视觉上很有意思,“车的状态很有意思,也很奇怪。”我请他进一步解释 “奇怪”一词时,赵小萌答:“有些车残破到没有意义去保留,但是为什么还保留它?”他用拍照的方式去探寻和记录这一状态。

在拍摄时,赵小萌主要的关注点在于自行车周边的环境和车主对自行车的施加物,比如车主的锁车方式、人对自行车造成的伤害,以及自行车的扩展功能——晾被子、放果蔬等。有时碰巧自行车主人在旁边,赵小萌会短暂与他们交流一下。交流内容不外乎询问为什么保存明显久已不用的自行车,自行车主人常常答:“咳,留着呗,说不定会用到。”

赵小萌镜头下的自行车,与其说是拍摄主体,不如说,是一个切入点,通过自行车的形态间接地反映人的一种状态。赵小萌认为人对车的态度亦是人在面对社会转型时的态度。“残破到没有意义保留,却不会丢弃,为什么?行为推导不出结果,那么行为本身就是结果。中国人可能更理解我说的这种状态,俗话讲‘好死不如赖活着’,任何有利用价值的东西就要继续利用,用来晾被子也行。而西方人相比就更实用主义,能用就用,不能用了就扔掉或捐掉,不会闲置。”赵小萌进一步解释说:“我小时候的北京,不是只为汽车设计的城市,路边全是自行车道。现在是人去哪儿都必须开车,步行和其他交通方式已经不是主流了。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再带动价值观的转变。现在社会认为一个人没汽车而骑自行车,就是没‘混’出来。社会用物质来衡量的不仅是自行车车主,也是一种对落后的生活方式的评判。”

赵小萌自小在北京复兴路的大院儿里长大。他对自行车最早的记忆是父母骑车带着他,后来渐渐长大他也有了自己的自行车,中学时骑的还是一辆女车。我笑问他,骑女车的他有没有被同学笑话,赵小萌答:“当时流行都骑女车,同学也骑。女车骑着舒服嘛,车筐在前面也方便。”他家在大院儿最西边,早晨上学,一路往东骑陆续会有骑车的同学加入,一伙儿人浩浩荡荡,“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样”。

赵小萌现在的家在德胜门附近。他照片里的自行车大多拍摄于德胜门附近和胡同里。但他并没有刻意把拍摄地点限于二环以内, “你发现了一个事物、现象后,再去留意关注,就会发现它到处都是。只是你从来没有去看而已。”

《人民日报》记者王文澜曾拍摄过80年代北京摩肩接踵的自行车盛状,再看赵小萌记录的自行车,不免让人感叹时代变迁之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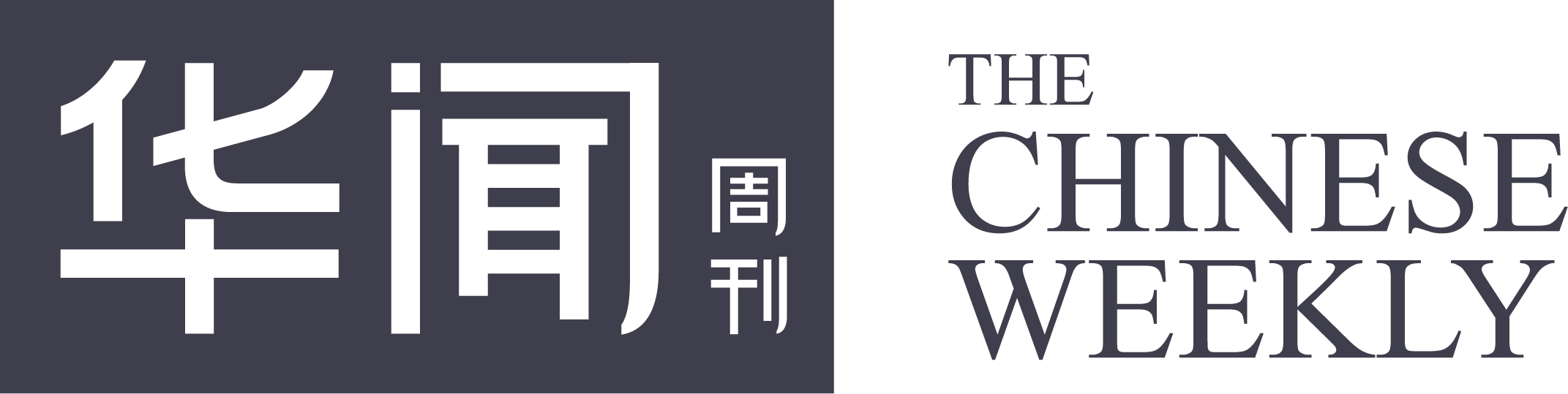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