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冷的周五夜晚,贾樟柯的《天注定》在伦敦西区的Odeon影院首映,等候入场的队伍甩出二里地,人们默默忍受着斜飞的细雨。同事们相约前往,因为《华闻周刊》这一期的封面专题与此片强烈相关;另一方面,贾樟柯的作品从未令我失望,虽然每次都让人难过纠结。
五年前,我坐在英国电影协会空荡荡的放映厅里,观看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影片内敛的叙事与压抑的长镜头,让放映厅里的空寂无边无际,无力的感觉几乎压垮了我,悲伤随之到来,顿觉黑暗的冰凉。当屏幕上那栋真实而奇怪的建筑以超现实的方式腾空而起,带来巨大的惊讶释放,我那压抑的情绪才找到了出口,而这个出口显然太小,与片子的沉重比起来,微不足道。
这观影经验让我担心,在去看《天注定》之前,我狠狠地吃了一顿辣,炽热的感觉升腾全身,我向影院走去。电影开演不久之后,我发现《天注定》似乎和贾樟柯以前的作品有些不一样。这是崭新的结构叙事,但情节却清晰易懂,四个故事的衔接缜密精妙,影片的爆发点和快感出现得很快。还没有经过漫长的压抑与蓄势,第一个故事已是血溅五步,快意恩仇。但这快感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几个故事里跌宕前进,过山车般的绝望失重感一次次裹挟而来,直到最后一个故事的最后一分钟,我的胸口都像坐了一头大象。
在首映之后对观众的采访中,同事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对于这部作品里体现出的形式和风格的变化,有人喜欢,有人失望,有人无动于衷,有人无底线地吐槽。这都正常,也不重要,观众的审美千差万别,老外对中国之真相雾里看花,他们就是把《天注定》看成惊悚科幻片也不奇怪。一部电影如同一个侠客,外部的招式未必看出他的功力,真正的力量藏在他不动声色的内劲之中。
影片的四段式结构带出四个相互交错的故事,在姜武、王宝强、赵涛、罗蓝山所饰人物的身上,你可能看出了胡文海、周克华、邓玉娇与富士康那些跳楼者的影子,但这些影子又与现实的人世若即若离。在这种既接近又疏离的联系中,你看见了他与她,也看见了你和我。
大海的反抗是林冲夜奔,三儿的出口是自我放逐,小玉的救赎是远走天涯,而小辉的解脱则是纵身一跃。在这样一个经济迅猛发展、工业文明无处不在的现代国度,信仰像狗一样流浪,希望像流浪一样漫无目的。其间的芸芸众生在生存的崖岸边挣扎,只有模糊的敌人,却有真切的怨怒,当光明被黑暗逼走,瑟瑟发抖的灵魂无路可逃,他们便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来实现自救,贾樟柯认为造成这些暴力事件的背后原因令人担忧,这或许是这时代悲剧的根源。
在影片中,彼岸高楼林立,而在此岸的冰冷现实中,却是城乡结合部的价值观混乱与群体道德崩塌。处于基层的农村几乎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毛泽东塑像、圣母玛利亚画像与传统文明的符号交织错杂。曾经庄重的苏联红军制服和中华国粹京剧的行头都成了妓女的包装,黑人在广州街头闲聊。小玉从蛇与美女的车厢离开,和母亲聊着惨淡的人世,周围的客人正谈论着“温州动车事故”,背景里传出央视播音员字正腔圆的播报……
人们曾经熟悉的社会话语系统和信仰体系,在科技发达的时代遭遇了无声的冲击,它们被新的情绪解构,然而在一个本应该被现代的文明体系所填补的空间中,当一桩桩事件被拆解,我们看到原因背后那真相的苍白,那是精神无可救赎之轻,是希望画地为牢之重。
由此,我看懂了电影中的真正主角,不是他与她,也不是你和我,这主角是这如荒野般的悲剧时代,我们无处可逃,却不愿抱团取暖。

在这期专题中,客座主编冰河与导演贾樟柯进行了深度的对话。同事林入采访了姜武、赵涛、王宝强和罗蓝山等参演的演员。其他的同事梳理了影片背后的新闻事件,并由此延伸出对中国这个时代的思考和质疑。在将所有的材料综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现象:受访的演员对于自身角色的理解似乎与我们想象中的并不相同,而贾樟柯导演自己最初的意图与作品传达出的意味也有所差异。贾樟柯非常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电影的奥妙就在于能够被不同的意义解读。
王宝强对于自己所饰演的民工冷血杀手如是说:“当时贾导是在重庆拍戏,拍摄的时候也没跟我说太多。只说了这么一个人物,在拍摄的时候我也不太知道,后来拍摄完成之后听他们说了我才知道还真的有这样一个事件。”
编辑部的各位同事关于小玉的结局有激烈的讨论。因为采访后发现,贾樟柯认为她是无罪释放,赵涛则认为她是刑满释放,而有更多观众却将其理解为畏罪潜逃。这很有趣。从导演完成这部作品的那一刻起,作品本身开始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它的影片性格的不确定性反而成就它极致的鲜活,面对一个多义生命体,去探寻其中人物的确定结局,会显得徒劳而多余。
首映结束后,在Odeon影院外的寒风中,一位观影的民众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拿起武器杀人,这是中国吗?”
“不懂中国本质的导演,拍不出这样的片子,而不了解自己的中国观众,也看不懂它深刻的内涵。影片之外,大洋遥远,在我那欲望无止境膨胀的家国,在那些盛大的繁华之下,藏着随处可见的危机。一个十几亿人相互倾扎的中国,在文明的背面越走越远。天注定的命运之下,一个国家注定的命运昭然若揭。”客座主编冰河在影评中的这一段话,是一个有劲道的收尾,也点出了本期专题的要义。
对很多西方的观众而言,中国的确是个遥远而难懂的国度,它辽阔又复杂。仅以来参加伦敦电影节的中国影片为例,贾樟柯的《天注定》和柴春芽的《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展现了属于死亡和绝望的侧面,而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则讲述了不食民间烟火的都市小清新与女人小哀愁。
局外人一头雾水,局内人百感交集。真正的中国电影,或许真的要呈现出这样多元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才能更全面把握各种价值观并存而交织的现实,而更为丰富而多侧面的表达,需要更多的艺术家去倾诉。让更多的中国导演、艺术家和文学家能够真实而真诚地表达,将是这个国家实现精神文明输出的终极责任。反过来说,各种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似乎也应该有更大的包容,因为中国不仅仅有你们想象中的这一面,同样也有你们不曾想到的另一面。
中国如同一部天书,是上帝和佛祖在下的一盘棋,而你和我,只是这个看似恢弘实则悲剧的时代棋子。本期《华闻周刊》完成的“天注定的悲剧时代”专题,为你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棋子的故事与命运,更给读者提示以更为深远的天问。因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懂得,是什么造就了如此之多的过江卒子,要么前进,要么无路可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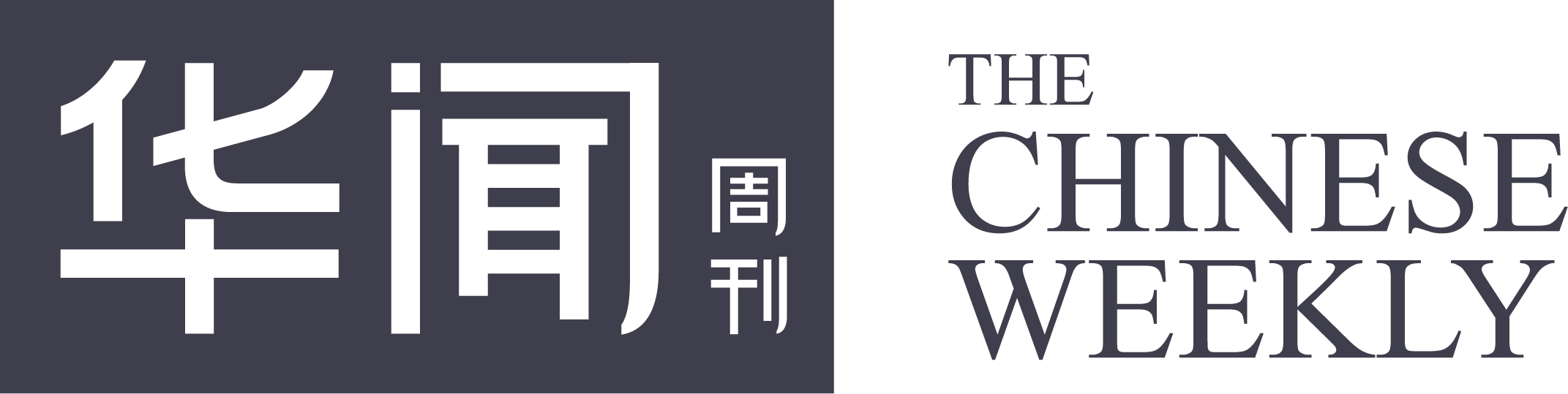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