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访者:
尚可,《电影世界》策划人、作家
《华闻周刊》:从《看电影》、《新电影》到《电影世界》,你的职业生涯曾经历过几次重要变化,背后有哪些原因?其中是否也反映了中国电影行业的变化?
尚可:我做《看电影》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那时候中国人看电影主要还是依靠租VCD。所以,这本杂志是一本普及的刊物,以介绍好莱坞和欧美电影为主。它的影响其实很大,我们后来接触到了不少北影、中戏的学生和毕业生,他们中很多人都说自己当时正是因为看了这本杂志,才去报的中戏、北影,最终走入了这个行业。此外,这本杂志还带起了一批影评人。
后来做《新电影》时,中国的国产电影已开始兴起,所以这本杂志更侧重于报道中国本土电影。这本杂志本身做得非常成功,后来是因为出品方中信文化的大格局出了问题,殃及池鱼,才使得它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
《电影世界》以前是我在哈尔滨的朋友们在做,到2006、2007年的时候它做不下去了,所以我才把它接过来做,直到现在。《电影世界》也是对国产电影、华语电影的报道更多。
从我接手《电影世界》之后,有过很多次的改版,改版基本上都是被迫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IT行业和新媒体行业的发展,改版是在想办法来适应读者的要求。
所以,从这三本杂志的变化中,我们确实能看到这十多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和中国电影观众的变迁。
《华闻周刊》:作为一个传媒人,你认为与“圈内人”(电影从业者)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最合适?
尚可:要做媒体,其实和这些“圈内人”保持一段距离是最好的,因为你在评价他们的作品时,需要保持客观的立场,你一旦和他们熟了,你必然要受到人际关系的制约,写的东西就没那么客观,没那么有意思了。
在做《看电影》的时候,“圈内人”我谁也不认识,那时候我可以客观地来评论他们,现在回头看,那时候写的影评是最好的。
但我现在已经和很多“圈内人”成了朋友,所以只能牺牲掉“影评人”这个角色了。我现在和“圈里人”关系太近了,你跟人家认识之后,你就不好意思骂人家了。
所以现在做《电影世界》,我自己并没有再来写影评,文章几乎都是我手下的编辑部主任、主笔和编辑们在写。另外,我以前只想当一个媒体人,现在我则想做一个创作人,比如我曾担任《无人区》的编剧、参与策划了《让子弹飞》,我还创作了一些小说。
《华闻周刊》:你以前评论张艺谋、陆川等导演的文章引发了很多关注,你所主编的《电影世界》最近有关张艺谋《归来》的文章,更是引发了热议。你认为自己在撰写或编选文章时是不是做到了客观?你有没有因此遇到压力?
尚可:我和张艺谋、陆川不熟,我评论他们的作品时,自己还是保持了一个客观的立场的。这次《电影世界》有关《归来》的批评文章并不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个人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对方的确是试图给我们的杂志一些压力,声称要封杀我们。我对这件事的态度是:电影好坏是一回事,但你不能不允许别人说话。
中国现在是媒体圈服从于政治、经济利益,很多媒体都是被买通的,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杂志,但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华闻周刊》:在你采访过的中国电影人中,谁让你印象最深刻?谁的采访难度最大?
尚可:印象最深的是姜文,他真想跟你交流的时候,愿意“掏心窝子”,可以跟你讲很多。
我记得和他聊得最深的一个采访是在2002年。那时候他的《鬼子来了》已确定不能在国内上映,他憋了好长时间,想找人把心里话讲出来。那次采访非常过瘾,他把制作《鬼子来了》的前后经过、他的思考和创作态度思想等等都跟我说了。我后来整理的时候,也觉得很有意思,后来这篇采访的效果也特别好,被很多人当成典范。
采访难度最大的是陈凯歌,他身上有种“贵族范儿”,刚开始接触的时候稍显傲慢。我第一次采访他,是托了我的一个长辈帮忙请他,他才勉强答应来。对待这一类型的受访者,必须要做好准备,如果你问了三个问题,他都不感兴趣,这个采访就会很快结束。
我当时采访他之前做了很多功课,把有关他的传记、报道和资料都看了一遍,基本上了解了他如何应付记者。我一开始采访就跟他聊“毛泽东”,聊“五·四”,聊“文革”,他感兴趣就聊开了。
他后来说从来没有跟记者这么深入地聊过,当然也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换到现在这个环境下,我估计他不会再说这么多了,因为现在中国舆论环境非常敏感,情况更复杂了。
《华闻周刊》:你认为中国电影行业这十几年发生了哪些主要的变化?
尚可:一方面是市场膨胀,一方面却是审查越来越严、资本对电影市场的介入越来越恶性,这使得中国电影出现了一种“扭曲”的局面:即允许你创作的东西和这个庞大的市场不成比例。
中国电影的市场规模呈现出几何级的膨胀,但同时中国电影也正在变成特权阶级所玩的游戏,各种利益的资本方在整合,这些大的资本集合起来之后,基本垄断了中国电影行业90%的资源。现在新人的成长空间变小,他们很难出头,现在的情况是,你必须要让资本认可你的故事,这使得大量的新人去跟风,很多人开始投机,创作质量不如以前。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电影审查制度。在中国现在的电影审查制度下,很多类型的影片是不让拍的,尤其是很多现实主义题材根本不能碰,这使得创作者离现实越来越远,真正有品质的东西特别少。中国电影现在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东西,就是如何哄老百姓玩儿,都是一些喜剧片、爱情片,类型少得可怜。在中国电影产业中,政治压力和资本压力得到了集中体现。
《华闻周刊》:你认为世界上成熟的电影工业模式中,有哪些方面最值得现在的中国电影行业借鉴?
尚可:好莱坞,甚至宝莱坞的模式,都可以供中国电影行业借鉴。现在中国电影行业的“工业化”还谈不上,你看现在中国电影行业中,那些好的后期公司、录音公司,很多都不是中国内地的,仍然有大量的空白和荒漠地带,在这些领域必须借鉴好莱坞等工业的模式。
具体来说,从创作开始就应该学,中国编剧现在都还是各自为阵,而好莱坞则有一个体系或者说工会这样的组织,它能够保护行业利益。而在中国,这些都体系和保护都谈不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好编剧能有保障,其他人全在碰运气。
中国制片人也有问题,现在懂账的制片人多,真正懂电影的制片人少。
《华闻周刊》:近几年,大量资本涌入电影行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尚可:坦白说,一些人投资这一行就是为了“泡妞”或者洗钱。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靠谱的、中途“黄了”的电影项目。
《华闻周刊》:这么多资本涌入电影行业,目前有没有相关的规管政策?海外资本现在一般通过什么渠道进入中国电影行业?
尚可:现在基本上是国内谁都可以来投电影,你只要先成立一个影视公司。大量资本涌入,这本身倒不是坏事。
海外资本进入中国电影行业的方式,一种是和中国影视公司一起合拍电影,另外一种是和中国金融领域的机构合作,做一个基金,然后用这个基金来投资电影。但外资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国家有相关的规定。
《华闻周刊》:虽然有很多中国电影到海外参加电影节,但进入海外院线的并不多,原因是什么?中国电影怎样才能走向世界?
尚可:中国一些商业片其实不需要走向世界,把中国的电影观众真正“喂饱了”,让他们看得高兴就行;另外那些“艺术家”型的导演,过去他们经常去参加世界各地的电影节,国外称当时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跟中国现在国内本身市场好、投资人多有关系,现在很多导演在转型,但成功的不是很多。
《华闻周刊》:你认为中国电影行业未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尚可:如果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能够实行分级制度的话,那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就了不得了。这一关如果不过,中国能上映的电影类型就会不断重复,这就像让我们看春晚似的,电影行业现在是一个月给你看十个春晚,没意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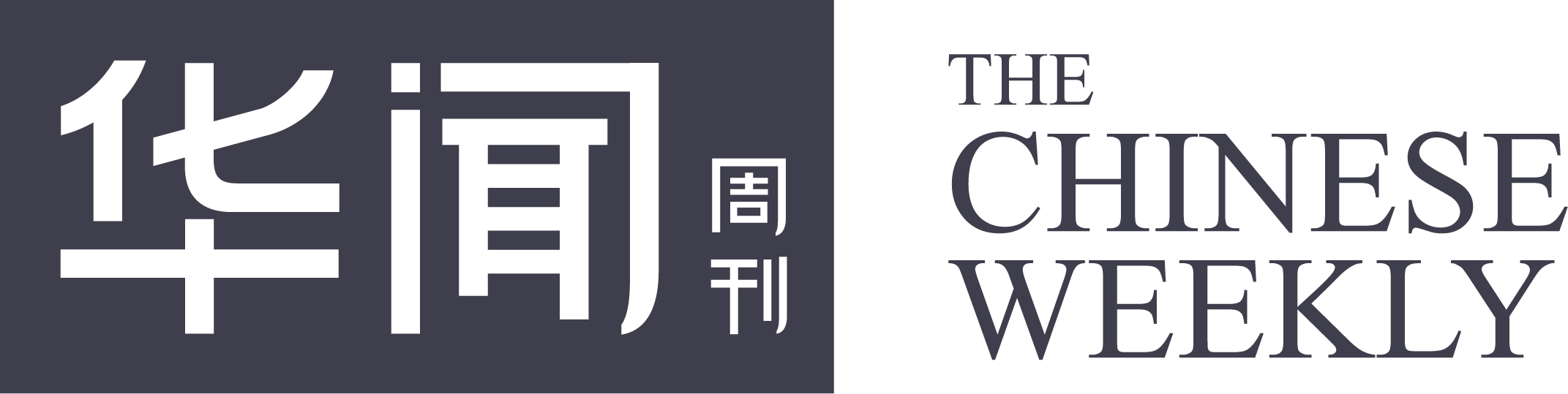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