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闻周刊:从贾樟柯一部《世界》转型到体制内也提供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很多可能性,赵亮也走入了体制内,包括您的《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也申请了龙标,通过了审查。你对自己在独立电影人这条路上的期待是走进体制内被更多的观众接受和认可吗?
杨瑾:主要看自己想拍的项目,符合什么规律去运营,是通过审查和更多观众见面还是自己随便拍着玩。
华闻周刊:你认为审查制度和九十年代比氛围有松很多吗?很多独立导演开始走进体制而不再一味的走海外资金的道路跟审查制度变松(如果有这个趋势)有关吗?
杨瑾:我感觉好像在变严。第四代还有《芙蓉镇》,第五代还有《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这样的作品,现在没有了。这些作品肯定是在电影局立过项,同意拍摄的。只是最后拍完了禁止公映。现在如果是关于文革历史,政治运动,同性恋内容的项目,估计连立项同意拍摄都很难。但是中国有盗版,只要是好电影大家都能看到。只是亏了出品方,所以越来越难有愿意投资这样影片的公司,所以只能看到很多脑残电影。
第六代很多发轫作品没有去审查,都是自己想拍就拍,所以也不知道审查是严格还是宽松。估计不会是宽松的。海外资金大多是一些基金资助,都是小额的。第六代的作品很多也是国内资金,很多投资人投资了影片血本无归,现在很难遇到愿意投资批判社会内容的电影了。或者说,根本遇不到。现在的有钱人很多,但是不投资批判社会的电影。年轻导演也有妥协。但我相信拍摄独立电影的年青人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所以说,走什么路线,跟项目有关,跟投资人有关。跟审查没有外界渲染的那么大关系。
华闻周刊:对于‘独立电影’或‘地下电影’这些标签你怎么看待? 您怎么认定自己的电影人身份?
杨瑾:第五代导演们经历了“禁片时代”。那时候要有大的制片厂,大的投资才能拍电影,如果没有电影局立项肯定无法拍摄的。只是拍完了之后,被电影局禁止公映。第六代导演们经历了“地下电影时代”,一个是没有立项就自由自在地拍摄了,二是题材上很多更多关注边缘人群。我相信这些片子虽然没有立项,但电影局也审查过完成片。当然是不能通过审查,不能公映的。中国没什么“独立电影”,我觉得独立电影对于中国导演来说是一种精神,就是独立地思考,永不妥协。这个妥协指的是金钱,是名声,是政治,是舒服。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导演。人都在妥协,但底线不同。
我就想拍一部电影,是我自己想拍的,不受任何约束,至少是在内容上不受约束。我想做的只是一名好的电影导演。
华闻周刊:您以前的电影《一只花奶牛》和《二冬》也是不走审查制度在外获奖,而到《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申请到龙标进入国内市场,您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从地下到地上的身份过度吗?
杨瑾:我的身份一直就没变过。申请了龙标不一定能进入市场,只是获得了公映权而已。能不能进入市场不是一个人选择的,是市场选择我的作品,是看作品是否有市场价值。而所谓“抵抗体制的身份表达”或是“艺术创作”其实没有分的那么清的。很多人拍电影是想创作一个好作品。那种为了摆姿态表达自己身份的导演拍不出什么好作品。
华闻周刊:你对自己观众群的期待是怎样?希望停留在小众还是希望能扩大观众群,会坚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商业化吗?
杨瑾:主要要看自己想拍的项目。符合市场还是不符合。每个人都在找一个平衡点,不可能做到完全坚持自我表达,能做到的只是尽量保持自己又希望得到更多观众。所以无论如何,都需要做一定的妥协,“独立电影”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
华闻周刊:你的《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是国内的投资人资金赞助,天画画天出品;但以前两部电影是不是走的独立电影的老路线---自筹资金拍片,参展,获奖来拿回拍摄成本? 你觉得依赖国际电影节来寻找独立创作出路的方式会影响到自己的作品吗?
杨瑾:《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一共四个投资人,两个出品公司——天画画天(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伊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之前的两部片子都是自筹的资金。我没觉得受到什么西方市场,电影节的影响。我都是由着自己的想法拍摄的。
华闻周刊:你觉得在做《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使用国内资本,并通过审查,在拍摄过程中有因为需要通过审查而做的妥协吗?如果不争取龙标,电影会不会更好?
杨瑾:《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这部片子完全也是由着自己的想法制作的,没有对审查制度做什么妥协,也不需要妥协,这个项目就是一个没有争议没有政治敏感度的项目,申请到龙标也很自然。
华闻周刊:你觉得摆脱海外资本回归本土市场是近年来独立电影新的趋势吗?您觉得这是一种好的方向吗?你觉得目前中国独立电影是怎样的生态环境?
杨瑾:《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除了国内的出品公司外,也有几笔海外资金,都是小额的基金资助。洛迦诺电影节,瑞士东南基金,美国环球电影基金等。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独立电影生态比较多余多元,大家都在想各种办法拍自己想拍的作品,走海外或是找国内出品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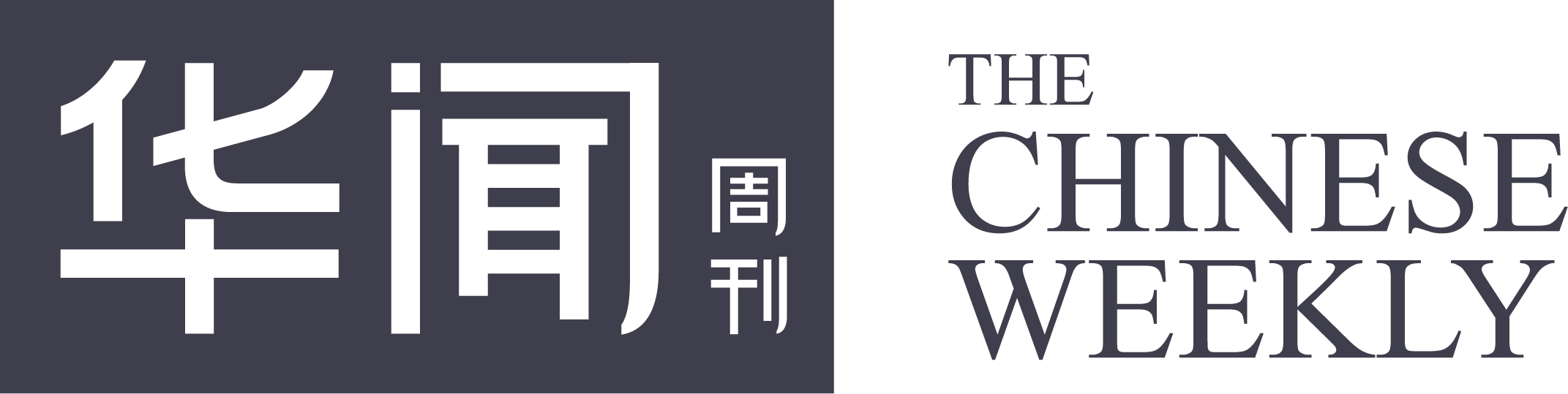 | 今日华闻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ihuawen.com 2010-2015 |